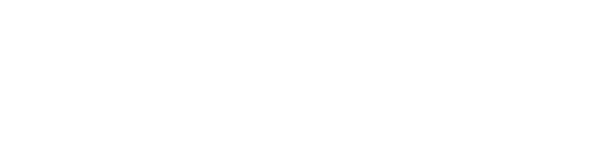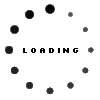遮住《ELPIS -是希望還是災禍-》劇名,打開幕前幕後的陣容,這齣劇應該是齣愛情劇。
主角長澤雅美與導演大根仁合作過電影《草食男之桃花期》;配角是外型帥氣的鈴木亮平與新生代真榮田鄉敦(他們這兩年內有接演愛情劇,都是演可愛女主角旁邊的可愛男配角);劇本由編寫過電影《天然子結構》與晨間劇《康乃馨》的渡邊綾負責;推動這齣戲的製作人佐野亞裕美,製作過坂元裕二的《四重奏》與《大豆田永久子與三個前夫》。
但即便《ELPIS -是希望還是災禍-》幕前幕後有著愛情劇陣容,但每集片頭結束時,畫面會打上一行字,告訴觀眾這齣戲與純情愛戀毫無關係:「本劇是受多起真實事件所啟發的虛構作品」。
這齣戲要打開的是劇名引用的典故:希臘神話《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s box),潘朵拉因好奇開啟魔盒,釋放了貪婪、虛偽、誹謗、災禍,但遺留了希望,而盒子裡的事物被稱作「ELPIS」,象微著人間有種種紛擾與良善,ELPIS是災禍,也是希望。
1992年,日本栃木縣足利市發生了一起女童殺害事件。一名父親帶著女兒到柏青哥店,父親玩柏青哥機打到一半,發現女兒失蹤了,焦急尋找後決定報警。隔天,全身赤裸女童的遺體,出現在柏青哥店附近的河濱,她的衣物被棄置在旁,上頭沾有體液。
當時的嫌疑人,是45歲的菅家利和,他除了經常出入該間柏青哥店,也曾經擔任幼兒園娃娃車司機,警方在他的住處搜到了色情錄影帶。中年獨居、曾是娃娃車司機、住處有色情錄影帶,讓警方決定鎖定有大眾對兒童性侵犯印象的菅家先生。
警方對他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跟監後,逮捕了菅家先生,因為透過當時剛引進日本的「DNA檢測技術」,警方檢測到女童衣物沾附的體液DNA,與菅家先生的DNA一致。證據確鑿,再加上菅家先生被捕時的認罪自白書──儘管他在之後審訊翻供主張自己無罪,以及警方問訊時遭受言語恐嚇並誘導認罪──多次受審後,判決有罪,判處無期徒刑。
但是,堅信菅家先生無罪的辯護人佐藤博史律師,力爭聲請重新鑑定與再審,終於,2008年,法院同意重新進行DNA鑑定,發現最初的DNA鑑定不夠精準,確實有誤。2009年,菅家先生已經過了17年牢獄生活,東京高等檢察廳以「新的鑑定結果可能證明被告無罪、符合再審條件」為由先釋放菅家先生。
再審時,確定無罪之際,庭內三名法官起立,當場向菅家先生鞠躬道歉。
這是日本近年來最有名的冤罪案件「足利事件」,也是啟發《ELPIS -是希望還是災禍- 》的案件之一。
而《ELPIS -是希望還是災禍-》將故事舞台架空在虛構的電視台,長澤雅美飾演的是因醜聞而被貶至深夜節目的主播淺川惠那,與原本圖謀不軌被人抓到把柄,而開始認真追查案件的年輕導播岸本拓朗(真榮田鄉敦飾),重新搜查,拂去上頭充滿厚重灰塵的真相,將足利事件報導裡會用簡單幾字「力爭聲請」的過程,拍成十集日劇。
在觀眾不會認真看待的休閒情報節目(ワイドショー)裡,意志消極的新聞主播,知道自己報導過的冤案失實,激起鬥志,決心重啟案件,讓冤案重回世人的面前;養尊處優的年輕導播,從未正視自己身邊的黑暗,渾渾噩噩,在一次機會,終於正視了自己,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便勇往直前。
在原本生活充滿無力感的兩人,不斷質問自己內心的正義為何,自己堅持的事物究竟是對是錯是惡是善,牽動彼此,彼此影響。而他們除了要應對電視台裡的僵化體制,更要對付更為龐大也更深沉的政治壓力,而他們的武器,正是傳媒。
這讓《ELPIS -是希望還是災禍-》拉向了更深的主題:新聞媒體第四權。作品風格多變的大根仁,在2016年以狗仔隊為題材的電影《SCOOP!》(改編1985年原田真人的電影《盜寫1/250 秒》)曾經觸及這個主題。當然,大根仁除了延展這個議題,更是直面官僚、警方──最後甚至直指政府腐敗。
長澤雅美近年野心滿滿,根據編劇渡邊綾訪談,長澤雅美讀到第三集劇本就答應演出──別忘了這齣劇用了大量篇幅描寫電視台面對報導不實的虛應。先不論這齣戲的政治爭議,在劇裡透過「厭食」暗示自我厭惡的長澤雅美,在一次次嘔吐戲與痛哭表演,表現淺川惠那的「迷惘」與「堅定」,確實可以感受長澤雅美在一連拿到兩次日奧演技獎項肯定之後的努力。
真榮田鄉敦的銳利眼神,表現出拓朗對人生原本的「空洞」,以及正義感爆發的「執著」。對應兩人時而頹廢、時而熱血,另一位亦正亦邪的角色,此次戲份不多的鈴木亮平也有不錯亮點,特別是不裸露的紳士性感。
反映並影射日本傳媒現況的《ELPIS -是希望還是災禍-》,在追查案件的同時,它拋出了多個沉重議題,讓觀眾跟著劇中角色感到鬱悶及困惑。確實,這齣戲不是要來解答問題,而是來質問──如同劇名副標「是希望還是災禍」。
它並不會給觀眾一個明確完整的答案,以及案件的最終真相(只有疑點更重的疑犯),而是,讓你去親眼看看箱子裡的「ELPIS」。一如愛情劇裡描寫的愛恨情憎,往往難以一言敝之,而《ELPIS -是希望還是災禍-》,要述說的是複雜的社會,複雜的政治,更複雜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