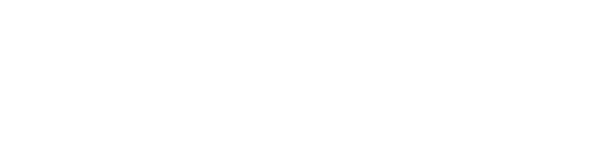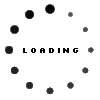1972年──距離今(2025)年53年前,與台灣近在咫尺的沖繩,漫長的「戰後」迎來另一波震盪:在長達27年的美治時代後,沖繩終於得以返還日本。
然而就連「返還」一詞,都像一根扎在沖繩人心上的刺。因為「返還」真正的主體是本土。對身在沖繩的人而言,是「回歸」。──《1972 渚之螢火》中,由高橋一生飾演的主角真榮田太一,用像是吞下了千言萬語的眼神看著東京出身的妻子真弓,淡淡地說。
讀歷史、背年表的時候,我們往往會錯覺那些發生的事件就像一個開關,切換過去之後一切就順利轉換。《1972 渚之螢火》以沖繩回歸不到20天前發生的一起搶案,帶出在那個「轉換」的時間點當下,人們的思慮、心機、不安、動搖,以及深藏其中的沉痛創傷。
「教科書上教的、和自己想像的,跟實際上經歷的人的體感一定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希望盡可能聆聽當地人的說法。」

以真榮田太一一角擔綱主演的高橋一生,在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時表示,因為喜歡沖繩,原先就對沖繩的歷史有所涉獵,然而在接演之後,實際來到當地拍攝的一個月期間,讓從前只存在他腦中的「知識」更加鮮明,化為一個人又一個人生命的歷程躍然眼前。
他也實際與當年曾經成為「戰果略奪者」略奪美軍物資維生的人談話,表示:「跟我談話的那名男性體會到的回歸本土前夕的世界,跟我想像的有著壓倒性的彩度差距。」「集團留下的記憶,和個人留下的記憶是不同的。這讓我更深切體認到,不管看過多少文獻、苦讀多少歷史,實態如何只有到當地才會知道。」
27年的時光,足以讓初生的嬰兒成為早就稱不上新鮮人的社會人士。當一整代的人在一個文化下成長、形塑,期待因為「不是美國人」而受到的打壓,能因為「成為日本人」獲得解放的同時,也面臨一直以來所認同的一切都將受到衝擊的不安。
在美治沖繩成長、前往東京念書就業,又在即將返還的時間點回到沖繩,對於真榮田太一,高橋一生形容:「他的自我認同的搖擺,就像是日本的縮影。」

1970年代,不只沖繩,整個日本都籠罩在國家認同的搖擺中。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安保抗爭、學生運動激化,正是在1970年代。高橋一生認為,當時進行抗爭的人,或許是真心相信在思想的碰撞下,真的可以改變這個國家。
而當時的日本這樣的狀態,或許也與一心相信沖繩回歸後就能獲得「自己是日本人」的定位,卻在調查搶案的過程中不斷面臨「自己究竟是誰」的扣問的真榮田太一極度相似。

在詮釋真榮田太一時,高橋一生用了一個小小的細節,呈現真榮田自我認同的動搖:就算回到沖繩,也一直說標準語的真榮田,在一場情感爆發的戲裡說了沖繩話。──情緒激動時說回熟悉的母語,是呈現角色情感很常見、也很真實的情境。
但高橋一生不想只是讓真榮田說回沖繩話。
「我去找方言指導,說『我想要講不標準的沖繩話』。就像顏料混入不同的顏料一樣,長年在東京生活、慢慢搞不清楚自己是哪裡人,已經再也回不去──我在想能不能用瞬間的言語來表達出那樣不可逆的狀態。所以那場戲裡說的並不是標準的沖繩話。」
高橋一生眼中的真榮田性格直率,不討好他人,也不會虛張聲勢。而他也在真榮田身上看到自己從前的影子:
「與那霸在談到真榮田時,說:『從以前就搞不懂那傢伙在想什麼。』也常有人這樣說我,所以我對這一點很有共鳴。大概是因為要說出口會很害臊、所以不太想把話講清楚的本性導致的吧。雖然會想不知道對方會怎麼想,最後還是覺得人家怎麼想都無所謂。演著演著,他那種『就算說了別人也不會理解』放棄解釋的樣子,讓我想到自己或許也有過這樣的時期。所以在詮釋角色的時候,某方面來說也是把自己的這個部分投射到他身上。」

與這樣的真榮田相呼應的,是青木崇高飾演的與那霸清德。相對於真榮田糾結於自身的認同,高橋一生說:「與那覇的角色非常堅定,卻也在如此動盪的時代下為之動搖。他和真榮田是完全不一樣的人。」
在時代的動盪中,面對來自內在、與來自外在的動搖,如此相對的兩個角色,在高橋一生和青木崇高的演技碰撞中相互映照。戲裡的死對頭,下了戲成為一起吃飯的好同事,如今劇集拍攝結束,高橋一生和青木崇高依然是會約到彼此家中吃飯的好朋友。因為選擇演出《1972 渚之螢火》,建立起彷彿延伸了真榮田和與那霸的革命情感,也像劇中對白所說:「我們都是有來自過去的一路傳承,現在才會在這裡。」
自子役時代累積了漫長的演藝資歷,2015年《民王》的貝原小秘書一舉爆紅至今過了10年,對於「被看見」的機緣,高橋一生心懷感激的同時,也認為這一切都是運氣。
「因為被發現了,也才能觸及以前一直想做的事。在想做的事當中,『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只有一小部分,是很大範圍內的一個小點而已。為了能觸及那個小點,被大家記住是必要的,而我想要提升這樣的機率。」
把握機會、提升「做到想做的事」的機率,努力被記住,如今他已經過了那個對演戲充滿飢渴、有戲就接的階段,現在的他在挑選參與的作品時,在意的是「自己參與其中的意義」,以及「是否能盡情燃燒」。
「以自己的肉身進到現場,這件事本身一定會在某種程度上磨耗身心。如果對一個作品怎麼樣都無法懷抱熱情,硬要自欺欺人演到底是也做得到,但總是會對身體造成負擔、會搞壞身體。所以我最近開始會想,既然如此,那就好好挑選能讓我燃燒熱情、盡情燃燒殆盡的作品。而且不這麼做,對觀眾也很失禮啊。」
全然投身演技、力求在作品中燃燒殆盡的高橋一生,對於自己身為演員的本質是否能確實傳達給觀眾,倒是十分豁達。
「有沒有傳達到都無所謂。因為我認為那是會因時代而異的,隨著大家解讀的方式、每個人的感受,和當下社會氛圍的改變,都會完全不同。把自己的想法傳達給對方,而且還是要傳達給所有觀眾,這樣的存在意義在哪裡呢?『高橋一生』這個演員的定位又在哪裡呢?我就算想知道也不得而知。大家會怎麼看待我,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所以我或許什麼都沒在想吧,甚至覺得大家愛怎麼解讀都可以。」
在訪問中笑稱讓他「徹底燒成灰燼」的《1972 渚之螢火》當中,籠罩在沖繩回歸日本的龐大命題下,歷史的塵埃尚未落定,形塑了如今的我們。而我們每一個選擇,也都將繼續形塑我們的未來。
就像高橋一生選擇接下這部作品,在真榮田太一的掙扎與追求之中,刻劃下了一部分「身為演員的本質」。透過真榮田太一,你看見的又是什麼樣的高橋一生?從他身上,又看見什麼樣的自己?
那也將成為形塑你的人生、傳承到未來的一部分。
現在,你可以選擇離開這篇文章,打開《1972 渚之螢火》,跟隨真榮田太一的目光,看看那片離我們並不遠的土地上,與我們如此相似的歷史。

參考資料:
Rakuten TV〈『1972 渚の螢火』の魅力&俳優として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語る〉
https://news.tv.rakuten.co.jp/2025/10/int-takahashiissei.html
Web eclat〈ちゃんと燃えて、ちゃんと燃えかすになれる作品に関わっていきたいと、ようやく最近思う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https://eclat.hpplus.jp/article/144018
ぴあ映画〈高橋一生が今、思うこと「世間のイメージに逆らい続けることが、消費に抗う最善の方法」〉
https://lp.p.pia.jp/article/news/439463/index.html